| 看扬中 |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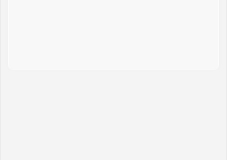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文苑 |
|
|
| |
|
□ 耿惠芳
“意气风发,唯我独尊,父母兄姐手中心的宝……而她自己,也自然地当自己是不可一视的女皇。”
这就是我,曾经的我,很久很久以前的我。
一直记着这样一句话:“人生的最大悲剧就是某一天突然从塔尖一下坠入谷底,这悲哀远胜过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毒药、爱情与谋杀。”从前的我一直觉得自己虽非天鹅,但也不会成为默默无闻的笨鸟,却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永远的丑小鸭。那是三十年前的车祸,它彻底推翻了我自以为顺风顺水的生命诺亚方舟!
当我的生命就要进入倒计时的那一刻,这时,有人出现了。
他守着一支针管,看着医生把我瘦削的残肢挽起,将殷红的血慢慢地输入到我的体内。他害怕我再也醒不过来,每天每天一下一下,摩挲着我肿胀的手臂。他的手指碰到皮肤的感觉,昏迷中我也会觉得痒痒的,像小鱼儿亲着我的脚趾头,像风儿吻过我的耳根,更像麻麻的那份名叫爱情的菜肴。
二十天,我的眼睛终于睁了开来……
一醒,我就不肯消停,我叨叨:“累了,累了,身子睡板了。”
他说:“好!坚持下,坚持下,挂完水我帮你翻身。”
“哎吆,出血了!针头处你没按好!”我生气了!那么大的生死劫难都还没磨掉我大小姐脾气。我嘟着嘴巴不看他。棉签重新按到了我手上。
“丫头,别总怪他。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好吗?”
病房门口的一位病友出声了:“你昏迷不醒时,他跪在医生面前求他们救你一命的啊!”
我哑然……
我知道他对我好,可我偏觉得没他烦我,我能做得更好。
如果说,一种观念的难以改变就是一杯毒药的话,毒药已经成了浩浩汤汤的湖泊,不用喝,就能将我淹没。
我便一直在自己破败的残垣边耕种,种希望,更种坚强,同时给殘垣裹上了一层一层荆棘,像院子里的牵藤草,蓬蓬勃勃。可我,却再没有能力给自己的残垣修缮。我可怜的肢体们,在时间里,依然在寒风到来时瑟瑟发抖……
我的心,玻璃般碎了一地。每一片,都冲着我龇牙咧嘴。
哪个人能接受这样的无情?
一晃三十年,生活的鸡零狗碎也早将过去的那些感动消磨殆尽,吵架便成了这个家永不停息的音符。
这次,上苍似乎要教训我的任性,非要给我一个下马威,莫名其妙地将我拽入了感染奥密克戎的第一方阵——高烧41.5三天三夜。
一边咳个不停,一边为我跑前跑后、端茶倒水、量体温、喂药片的还是他!还是那个从没提过爱,而且是从来都喜欢互相埋怨的那个他!
有了这次体验,我有时会问一声:“累了吧?”“不累,不累,我还得去医院帮你配药,你吃的药没了。”这个说不累的男人,真的将备好我的药当成了他第一要务:药快没了赶去配,到吃药的点了会放下手中所有事将药塞进我嘴巴里,再端上水。我常不记得,他却从未忘记过。
我躺床上已十天,今天试着起床。刚走到门口:“快躺好去,再着凉了不是开玩笑!”
他急了,再次拿起体温枪量着我的体温,不发热,又不放心,伸出手再次摸摸我的额头。嗯,我还真成了被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小女人了!
这个遇事优柔寡断的男人,在人人自危的病毒面前,却选择了近距离服侍,那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与此相比又何足挂齿?
此时,新春的月色,浓得像新疆的马奶子酒。它们流淌在窗外的杨树上、榆树上,也流淌在他临窗的背影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