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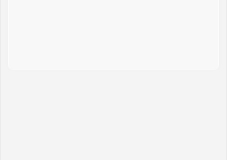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文苑 |
|
|
| |
|
□ 范选华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 《看戏》,说了童年时看戏的诸多乐处。其实于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而言,对看戏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并不多,而记忆深处最能勾起少年滋味、念旧情绪的,还是看电影,看露天电影。正巧,上周“微扬中”短视频“流金岁月”推出了一期“老物什讲述老故事”,说的就是老电影放映员的那些陈年往事。
放电影辛苦看电影欢。看完这些老放映员的故事,我突然想起一年之前曾经写了一篇半拉子文章,关于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于是找它出来,续写而就,就算是呼应“微扬中”的应景之作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大多比较顽劣。暑假白天泡在水里,捞鱼摸虾,摸螺子踩歪歪(河蚌),寒假成天在冰面上打“李逵”(陀螺)、凿冰钓鱼(那时的天真冷,河里的冰很厚,经久不化)。上学期间,放学后除了父母布置的“必修课”寻羊草(“寻”念成qin)、捻柴枝枝,就是打“掼炮”、打香烟壳子,跳绳子、颠“格子”,后来还发展到打 “弹子”(玻璃球)、搭“钱墩子”(用硬币摔在墙上,然后用拇指和中指拼命撑开来量跨,一分钱算一跨,以此类推,量自己的硬币和对方硬币的距离,只要能够得到对方的硬币就算赢)。那时的我们,白天生活可谓丰富多彩,暑假夜间乘凉也颇为热闹,其余时间太阳落山后只能各回各家,用现在的词叫“百无聊赖”。躺床上就会想,哪天能有电影看呢?
看电影,是我们这一代人儿时最大的愿望,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如过年一般的快乐。虽然乡里的电影院三天两头放场电影,但几毛钱一张的电影票还是让很多农村孩子在电影院外无奈地徘徊,总是要等到快散场了,拦票的才会开恩放你进去看个“剧终”。所以,要想酣畅淋漓看场电影,露天才是王道。
大队放电影,或许是上面安排的,就像现在的送文艺下乡。但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规定,只知道过段时间就在大队厂外的公路边,挖出两个坑,树起两根毛竹。放学路过时看到这,心中顿时一凛,太好了,有电影看了。于是飞奔回家,飞快作业,飞一般地干完调猪把食等家务,风卷残云草草扒两口饭,就飞一般地扛着板凳去看电影。即便如此,靠近电影机的位置总难抢到,这时心里顿生懊恼,早知道放学回来就去占位置。那时的我们都以能坐在电影机旁而沾沾自喜,或许是位置正点,看电影画面可以不偏不倚;或许是能近距离看到放映员倒片、放片、断片维修,运气好的还能捡到一段断而被弃的胶片;或许是能更清晰地听到电影机那咔咔哒哒的“喘息声”,闻到电影胶片受热后特殊的“焦糊味”……孩提时代的心思其实很简单的,也就是满足好奇心而已。随着自己慢慢长大,有时去晚了实在没办法,还能到银幕背面凑合着看场电影,位子不位子倒是无所谓了。
夜色笼罩乡村,电影快开演了,丢下饭碗的大人们开始陆陆续续来到大队厂,一时间人声鼎沸,喧闹异常。大人们边扯着喉咙呼唤自家孩子小名,边死劲往里挤着,碰到撞到别人,免不了“杠桑吵死”几句。年纪大一点的老人们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些闲话,有时还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带孩子的女人们看起来是在和别人说说笑笑,视线却停留在年岁尚小的孩子身上,时而还会突然去责骂不听话到处乱跑的大孩儿。对于那些青春萌动的尚未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看电影是最好的约会和表白时机,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人堆后面,女孩儿的羞涩,男孩子的热辣有时尽显无遗。卖瓜子、蚕豆、炒米团等零食的小贩们在小摊前亮着一个手电或者 “虾子灯”(风灯),攒着劲地吆喝着。最开心的还是那些年幼淘气的孩子们,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要么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要么是绕着场子你追我打,可劲地喧哗。
电影终于开演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瞬时变得鸦雀无声,天上的星星静悄悄的,地上的人们静悄悄的,只有放映机投射出的光影在变幻,只有荧幕上的人儿在说话,角落里偶尔传来不听话的孩子的叫喊声和大人的呵斥声。
那时放电影,一般都是先放一部短片子,扬中话叫 “加演”(也有“假演”一说,意为不是正片)。这“加演”有时是动画片,有时是纪录片,还有直接放幻灯字幕的,放的最多的还是农业科技普及方面的。“加演”虽短,却影响心情,放了一会儿,孩子们开始不耐烦,大人们也在咕哝。这时,正片登场。记忆中有《英雄儿女》《地道战》《月亮湾的笑声》《红楼梦》《五女拜寿》《少林寺》等很经典的影片。
那时放一部影片,中途要停好几次,为的是换拷贝。一部影片往往由三到四盘拷贝组成,装在一个拷贝箱里。在放第一盘拷贝时,放映员要把第二盘拷贝拿出来倒片,倒好的片子等会儿装进电影机接着放。有时,同一部影片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放映,还需要“跑片”。“跑片”是有讲究的,大多是一个晚上放两部影片,我们这先放的这部片子是异地要放的第二部片子。“跑片”的路途如果远一点,看完第一部影片的人们就只能等着。这时,大队厂里再一次人声鼎沸起来,有人开始对播放的电影评头论足,有评论演员的,也有评论角色和剧情的,还有对那些反面角色骂娘的。有人在询问下一部电影是什么,犹疑着要不要继续等下去。有人又开始扯着嗓子找那些像泥鳅一样到处乱钻的小孩……直到电影机旁发出响亮的“来了!来了!来了!”,人们终于再次安静下来,慢慢沉浸到剧情中。
看电影之所以能让人记忆深刻,一方面,经典永难忘,但更多的还不是因为情节精彩,而是情结难解。与我一般大的人,都会有跟看电影有关的刻骨铭心的故事。我看电影跑得最远的,是从永胜跟在大人后面扛着个板凳,跑到十几里路之外的东新港,为的是看那宽银幕电影《少林寺》。第一次看到两个放映机,中间不用换片,从头放到尾,第一次看到两个银幕连在一起被风吹成弧形。看电影最闹心的是,看到一半被吆喝回家,心还在那里,只能躺在床上竖起耳朵 “听电影”。最虐心的是,电影放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停了电,放映员还没带发电机,我们走也不是等也不是。最窝火的是,公路边看电影突然来个车,大灯照着,喇叭叫着,大家极不情愿地起身让行。最戏谑的是,扛个板凳大老远地跑过去,却被告知今天不放电影了,沮丧之极,回家告诉爸妈今天放的是 《战斗英雄白跑腿》。
说到看电影,怎么也绕不过放映员。那时的电影放映员,在我们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在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他们下乡放电影都是骑自行车,穿戴也比普通老百姓高级,看起来就像个干部,至少我觉得有点像老师之类的文化人。他们来放电影时是大队里的座上宾,大队书记等人陪他吃饭喝酒,坐在电影机旁,我能闻到放映员打嗝后的酒香。他们还是快乐天使,不论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雨,熬夜坚守,给乡村带来欢声笑语,给孩子们烙下浓浓的乡愁记忆。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永胜乡的几位放映员的模样,依稀记得群众恶作剧给他们起的昵称别名。时间可以流逝,他们也已老去,但他们带给我们的快乐长存。
依循着一部部电影的引导,在我的孩童心灵里,在简单地对“好人”“坏人”的分辨和爱憎中,懂得了许多朦胧但却终身受益的道理。从最初的黑白电影到后来的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我深深沉迷其中。露天电影,在那段物质与精神生活贫乏但很质朴、令人回味的岁月,陪伴我走过十几个春秋。
考取大学那年,村里为我放了场电影,播下了崇学向善的种子,也让我永远铭记在心。前不久,从三茅去外地,天色已黑,路过一新村正好在放久违了的露天电影。于是赶紧停车,找个空处,坐到了一大帮神情专注的孩子中间。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回到了带给我们快乐和真善美的露天电影时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