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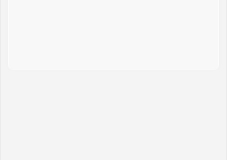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文苑 |
|
|
| |
|
□ 范选华
农民,就是种田的,农民的孩子,都是在田里长大的。年少的我们在田里栽过秧、拾过麦、沉(扬中话音,意为打洞施肥)过化肥、寻(扬中话念“勤”)过羊草。调皮的我们在田间界岸上偷吃过青蚕豆,洘干田边腰沟槽子里的水,捻螺螺捉鱼虾;和邻村的孩子在大田的河边上掷(扬中话念“登”)过烂泥“打过仗”。渐渐长大的我们更是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父辈们在田间挖“干子”、起垡头的沧桑和艰辛(垡,普通话读fá,扬中话念guā。垡头,扬中上洲话有说成“翻垡guā”的)。
金秋时节,稻子上场后,麦种下田前,农家青壮年开始挖“干子”。其实,挖“干子”的本意不是要起垡头,而是清沟理墒,让麦子生长时不受水渍之害。起垡头只是“一事两个档”,物尽其用罢了。
夏末秋初,天气微凉,太阳却依然很毒。蓝天白云下,一行行整齐的稻根桩在不经意间已长出绿油油的青苗来了。烈日下,在这郁郁葱葱的田间挖“干子”,闻着泥土和青苗香气混杂的味道,也是痛并快乐着的。
我记得的挖“干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瓦刀起槽,然后再切块起垡头。这种瓦刀是安装在貌似独轮车车架子的木头装置上,年幼的我坐过这玩意儿,我的份量刚好能让瓦刀插没在稻田里。记忆中,父亲在前面用绳使劲拖行瓦刀架子,母亲则在后面扶着,还要盯看着坐在瓦刀架子上的我,防止掉下来被刀伤了。几行“干子”槽开下来,父母亲已是浑身湿透,汗如雨下。这才完成了工作量的一半,接下来父亲还要用大锹切块起垡头。三四亩地干完,手上全是血泡。
挖“干子”还有种方式,不用瓦刀靠大锹,一个人作业。大锹,是农家必备的工具,弯弯长长的,装一根木柄,扬中人也有称之为“舵锹”的。曾有人说,扬中挖垡头的锹是沙洲县塘桥镇农民发明的“塘桥锹”。我上网查询了一番,“塘桥锹”跟我们扬中人口中的“大锹”还是有区别的,“塘桥锹”上下一般粗,而扬中“大锹”是上窄下宽,“大锹”是海安、如东等地发明并流行的,就近传到一衣带水的扬中也很自然。再有,我们扬中人骂调皮的小孩“革大锹”“革锹拐子”也都表明,扬中人用的锹是“大锹”或称“舵锹”,而不是“塘桥锹”。因为现在种田都是机械化作业,这种大锹已经很少用到。
大锹挖“干子”是“老把式”农民的基本功。先用尼龙秧绳按照所要的垡头尺寸在田里拉好放样,再用大锹沿着秧绳“摇”出两行沟槽子,再将沟槽子里的“干子”一块一块地切块、起出。这种方式挖“干子”不仅要费极大的体力,还必须要有相当的技术。挖下去的每一锹都必须垂直平行、不歪不斜,挖出的每一块垡头必须厚枵(xiāo薄)一致、不厚不枵,而且四面都要光滑平整。特别是最后起垡头的那一锹最显功夫,起的不好,不是断的就是碎的,那就不是垡头了。
不管哪种方式挖“干子”,挖出成形的都叫垡头。挖好的垡头就近堆在地势较高的界岸上码放成垛、进行晾晒,块与块之间还要留有一定的空隙,以便通风透气。待垡头晾干泛着白光时,又一轮艰辛的劳作开始了——挑垡头。父母挑垡头大多在晚上(白天到厂里上班),那场景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有时还会在梦里闪现。皎洁的月光下,父母挑着一头码放五六块垡头的笿子,在青草浅覆的界岸上疾走,一路上那优美的挑担号子在乡间悠悠飘荡。垡头挑回来后,父亲靠着厢屋沿墙将其一层一层码放整齐,最后用厚实的稻草苫盖封顶,以防雨淋。
田间的垡头,多是用来垫猪窠、垫羊窠,也有用来“蒙”竹窠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中下洲的老百姓几乎家家养猪,还有许多养老母猪的。我家也养老母猪,母亲后来笑谈,不养老母猪你哪来的钱读大学。猪的吃喝拉撒睡都在猪窠里,在猪窠没有硬质化改造之前,都是用垡头和稻草垫窠。那些日子里,父母几乎每天都要搬上几块垡头,用钉钯将其敲碎耙匀,在猪窠里垫上一层。除了猪窠,羊窠也是需要垫的,而且羊与猪相比其活动圈子更小,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那一方小小的灰堆上,所以用垡头垫窠的频率也不低于猪窠。
垫窠苦,出窠挑灰更苦。那混合了猪粪、羊粪、青草、瓜藤等成分的垡头土,经过牲畜的反复踩踏,是垩田的宝贝,也是农人挥之不去的重负。梅雨季节,“双抢”来临,做秧田、耙大田,都要猪窠灰“打底”。猪窠里又湿又臭,父母亲弯着腰,在闷热的猪窠里出灰,不一会便衣衫湿透,浸染着猪粪味道。顾不得太阳的热辣,他们还要马不停蹄地将猪窠灰一担一担地挑送到田头,用手均匀地洒落在田间,拖拉机耕翻后,水一上,便可栽秧了。转眼到了“秋收冬种”时节,人工坌田拊麦种,便又有一次“出灰”“挑灰”的辛苦劳作。临近年关,麦苗长出,需碾压施肥,一年中最后一次出猪窠灰就在这个时候。于是,清冷的一大早,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升腾的时候,埭前屋后就响起了乡亲们挑灰下田的脚步声。
“蒙”竹窠,是扬中人巧用垡头的独特之举。秋日,挖“干子”起出来的碎垡头,直接用笿子挑回来倒在竹窠里,一层垡头土一层麦芠子(扬中话,指麦芒),层层叠叠,几场雨过,垡头里的有机质慢慢渗透开来,滋养着那些沉睡的笋。春雷滚滚,笋儿从垡头土里拔节而出,健硕闪亮,有的长成扬中农家的“哑巴儿子”,有的成了扬中人舌尖上特有的美味。
垡头,扬中人也曾经用来砌墙。我没见过如何堆垒垡头墙,倒是在垡头墙上掏过蜜蜂洞。装着油菜花的玻璃瓶口对着蜜蜂洞,用竹林条子将蜜蜂赶进瓶子里,那种快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扬中孩子。
虽没见过垡头砌墙,但我认为,垡头“支大灶”跟垡头砌墙应该是一个道理。老丈人生前做瓦匠谋生,是十里八乡不多的能“支大灶”的手艺人。年过七旬的他有一天提出来要翻房子,我第一个应允了,不仅出于孝道,还在于他有支个新灶的想法,这让我心生期待。
那年秋天,老丈人的新屋装修得差不多了,厨房里除了支大灶的地方也都贴好了地砖。事先看好的支灶日子快到了,老丈人到埭头高岸上挑来数十担黄烂泥,在新铺的大理石场上碾碎起堆,在堆尖挖坑成火山锥状,加入水,掺进麦芠子,还有从理发店里要来的头发丝,用钉耙来回拉扯搅拌,直到所有烂泥浸透、铺开成形。待烂泥稍干,老丈人穿上套鞋,一只手拎一个笿子,脚踩在笿子里,一脚一脚地来回踩着,烂泥紧实后,再用瓦刀泥平。等到烂泥半干,遂拉绳切块,做成垡头。秋风艳阳,这垡头干得也快。等垡头干透,泛着青白,黄道吉日也到了,老丈人欣欣然开工支灶。
老丈人支大灶很是讲究。除了灶脚、灶面、灶门、烟囱等几个部位不得不用砖头以外,其他部位全部都用的垡头。看着老丈人有板有眼地垒着垡头,我好奇地问道,这垡头支灶跟垡头砌墙是一样的吧?老丈人头也不抬地说,垡头砌墙直里乒乓的,垡头支灶要砌成圆形,复杂的多了。我又不解,那为何不直接用砖,方便得多。老丈人肯定地说,黄泥垡头围成的炉膛,比砖砌的锅膛要“快”得多。我用文乎文乎的话来理解,就是泥土与火焰的对话,能既快又好地烹制出属于农家人独有的乡间美味。
如今这垡头砌成的大灶还在,支灶的人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