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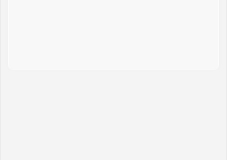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文苑 |
|
|
| |
|
□ 边震遐
1953年春,我随志愿军九兵团政治部摄影组长王纪荣到上甘岭。说是我随他,实际上是他带着我上战场。
作为一名新四军老兵,王纪荣富有戎马经验,在入朝参战之前,就已经研究过朝鲜战地的敌我形势,所以一到新岗位,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我们的目的地非同寻常,是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此时的上甘岭,虽然已结束了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战斗依旧在延续中。
要到达上甘岭的五九七点九主阵地,必须通过密集的炮火封锁。王纪荣命令我不许同他靠得太近,两人要拉开距离,一人出事还有一人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也可以向部队报个信。王纪荣毅然走在前面。满山都是被炮弹和航弹反复犁过的松土,攀登极为困难。口渴难熬时,贪喝石缝中流出的细泉,带有呛鼻的尸臭。躲过阵阵炮击后,在接近第一道交通壕的时候,又一排大口径曲射炮弹带着啸声凌空落下,王纪荣迅速卧倒滚进一旁的弹坑中。硝烟散去,我不见了他的身影,狂呼着扑上前去。见他已被泥土半掩,身边有被炮弹炸起后坠落的尸骸,断骨中淌着墨绿色的腐液。
王纪荣脸色惨白,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想架起他上路,他缓过神后喘息说,你架不动我,我没有伤着,是累的,歇一会儿就好,你快进交通壕,免得再来炮弹一块完。我拼命爬进交通壕,向哨兵通报了王纪荣虚脱在弹坑中的危情。哨兵立刻叫来两名战士,把他架上阵地,进入了坑道。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喝过一大杯水,就露出笑容说:“没有三分三,哪敢上梁山!”
王纪荣以他的诙谐让我沉着。在残酷的战场上,豪爽能够激励斗志,而诙谐则能舒展胸怀,催化智慧。
按照时令,该是春暖花开的仲春季节。可是上甘岭战场的情景却让人触目惊心。
上甘岭是五圣山的前卫,一旦上甘岭失守,五圣山也就难保。上甘岭的攻防鏖战,势不可免。
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曾随部队到过上甘岭,处处都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此时的上甘岭,全部植被早已为炮火摧毁殆尽。五九七点九主阵地的山顶标高降低了三公尺,最初的第一层坑道变成了交通沟。当九兵团所属部队接替上甘岭防务后,像露天煤矿般层层叠叠漫山遍野的遗体,尚未清理完毕。我睡觉的坑道支洞,是一位连部的文书好心让给我的,掀开一件旧大衣和一条防潮的狗皮毯子,就发现了一个烈士遗体的背脊。在交通壕外的任何地方,几乎遍地都留着碎骨碎肉,每每见到一截皮带,一片衣角,扒拉扒拉就是一个或几个遗体。一连好几天,我吃不下饭,光喝水,嚼一点压缩饼干。王纪荣早就看在眼里了,他悄声对我说:“看到烈士,就多想想自己肩上的责任。不吃饭,岂不等于向敌人缴械投降吗?”
话不多,却震撼。我很快适应了严酷的阵地生活。一天晚上,我登上山顶拍摄我炮兵夜袭敌阵的场面。我在拍完照片回主坑道时,遇上敌炮还击,地面震动,不小心滑下山坡,如果滑到山脚就必死无疑,不被炸死也给松土活埋。我便本能地张开双臂,想拉住一个树桩或石棱,结果拉住的是烈士的一只手臂,受惯性冲击,这只手臂让我从泥土中拔断,却阻止我继续往山下滑落,及时救了我的命。照明弹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只手臂已经干枯发黑,手指上还套着五个木柄手榴弹的拉火环。
次日清晨,我特地约王纪荣一同到了这位烈士所在的位置。王纪荣庄严地向我下达“立正──敬礼”的口令,两人同时向烈士致了军礼。王纪荣又口吐妙语了,他说:“小边命好啊,关键时刻,烈士也伸手救了你一把。”
据清理阵地的战士告诉我说,经现场勘察,像黄继光一样用身体堵敌人碉堡射孔的英雄,光在五九七点九阵地上,就有七名之多。遗憾的是这样的烈士在投入激战之前,为了保密需要,身上所有的部队番号和姓名都清除干净了,牺牲后也就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
当时,据守在五九七点九阵地的狙击能手张桃芳,已经创下单人单枪毙伤敌人81名的记录。消息发表后,有人怀疑说:狙击敌人怎么像拾麦穗一样容易啊?王纪荣说,历来打仗统计战绩,对阵双方都很难做到绝对准确,古时候战胜方先用斩首级计数,实在不方便,后来改用割左耳朵计数,也可能出差错,我们到实地看看就清楚了。
4月9日拂晓时分,王纪荣决定带我到前哨班去看个究竟,验证狙击实况,直接为张桃芳拍摄现场狙击照片。
天黑后,王纪荣和我动身返回主阵地。主阵地南坡的交通壕早已被敌炮炸平,敌人随时用机枪与火炮进行着不规则的封锁射击。这回王纪荣让我走在前面,嘱我翻过山梁后到连部坑道里等他。当我一跨进山梁上的交通壕,就急切地盼望着王纪荣的到来。等啊等,大约等了十分钟不见他的踪影,而枪炮声响得正紧。引颈望望,南坡上一片烟火。我想了想,不能干等,必须赶快向连领导报告,好派人寻找和救援。我跌跌滚滚地钻进主坑道,一定神,竟发现王纪荣正在烛光下啃馒头,还冲着我笑哩。他说:“我眼看着你的身影翻过了山梁,就放心了。敌人的炮火很猛烈,火光中我突然发现一个黑窟窿,想到是坑道火力点的射击孔,便钻了进来,抄近路沿着垂直坑道摸到连指挥所,我啃完一个馒头就打算去接你,你就来了。好啊好啊,快趁热吃馒头。”
王纪荣带我深入前哨狙击阵地采访,原是瞒着阵地领导的,因为阵地管理制度严格禁止非本部队作战人员去前哨狙击阵地。王纪荣出于一名老记者的责任心,才决定来个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出了这一起严重事故后,事情也就瞒不住了。连长和指导员先是表扬我们二人深入前沿采访,给部队带来鼓舞,接着又狠狠批评了我们二人“无组织无纪律”“犯自由主义”,还要求我们不得向上级机关说起这件事,否则他们就要挨处分。王纪荣大包大揽,承担了全部责任。
硝烟弥漫的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阵地,敌人称为“伤心岭”,而志愿军却称为 “红山峰”。对志愿军来说,只因人人都有视死如归的浩然气概,它不但不是地狱,而像一座原子反应堆,充满着热和能,活力无穷,尽管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牺牲或负伤,可是见不到叹息和哭泣,到处生机勃勃,有笑声有歌声。屯兵坑道布置成“文化室”,展览着来自祖国的慰问品和慰问信,每周六有战士们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四通八达的坑道构成地下长城,连接着整座大山的突出阵地。几条主要的交通壕都用炮弹箱的木板写上“北京路”“和平街”之类的响亮名称。阵地广播站在枪炮声的伴奏下,向阵前的敌人传递真理之声的同时,也向战友们播放动听的音乐,早上播《东方红》,晚上播《王大妈要和平》,还有西洋音乐和民歌民乐。
十多天之后,王纪荣转往炮兵部队采访,我因为还要采访冷炮射击活动,并等待小部队出击的报道,继续留在上甘岭,一留竟留了27天。
小部队出击是一次异常重要的任务,由师部侦察连连长带队,团参谋长坐镇指挥,主要目的是必须抓回活口,了解新换防敌军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参加了庄严的出征仪式,半夜结束战斗,在报告歼灭敌人两个加强班并捕获两名俘虏的同时,带队的侦察连长却不幸牺牲在凯旋路上,遗体被战友们背了回来……
在离开上甘岭之前,我完全习惯了与战士们一样的生活,战士们也把我当成真正的战友,写家信写情书也求我帮忙,还把美军避弹衣的尼龙瓦和缴获的照片送给我作纪念。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只是身上长满虱子,阵地上的清水是徒步运输员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没法洗脸洗澡洗衣。回到机关,脖子上的污垢能像锅巴似的揭下,脱下棉衣时,还发现棉絮中带回了两块炮弹片。王纪荣还特地为我拍了一张照片,有意拍下衣袖上钻进弹片的破口,说是有点纪念意义。
王纪荣真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哥哥。他知道我在奔赴上甘岭时,身上藏着一份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考验我,如果牺牲在战场上,请求追认我为共产党员。王纪荣竟用调侃的口气对我说:“现在不是刘胡兰的时候了,不到18周岁不能入党,你就是牺牲了,顶多追认你为优秀青年团员,也不会追认你为共产党员的。趁活着好好干吧,动不动想到死多没劲啊!”我当时挺泄气,暗中埋怨老王不理解我追求进步的积极性。不料回到后方,兵团政治部机关党委就收到驻上甘岭部队党支部的一封报功信,偏偏只为我一人报功,我心里就有点数了,肯定是王纪荣在我背后出的主意。我问他,他就狡黠地笑了,他说:“首先是你真的有功可报,不是假的。连长和指导员都要我回机关后给你报功,我说我报功没有说服力,还是你们直接报吧。你不是想入党,要求党考验你吗?这个报功信也就是一份考验证明书啊!”
要感谢老战士王纪荣引领我到了五圣山下的这一块上甘岭圣地,无异于指导我进行了一次战地采访的强化训练,更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王纪荣是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二十四军《火线报》、《华东战士画报》摄影记者,参加了华东战场各大战役的采访报道。在上甘岭地和王纪荣相处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独立执行任务了。
随即,我就单独深入到激战中的丁字山阵地,又参加了高炮对空作战和坦克部队袭击敌阵的现场采访,又参加了最后促成和谈签字的夏季反击战全过程,登上了刚占领的注字洞南山阵地。除了拍摄照片,也开始写作战地通讯。有了上甘岭的27天,我才体悟到生命的易凋和慷慨捐躯的价值所在,也懂得了什么叫战士,什么叫战地记者的应有品格。 (注:本文有删减)
王纪荣,扬中人,1953年1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先后任总政联络部干事、北京市革委会政治组干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办公室副主任。
边震遐,浙江诸暨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共党员,一级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