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专栏 |
 |
| |
 |
人大专栏 |
|
 |
政协专栏 |
|
 |
法治扬中 |
|
 |
扬中人医 |
|
 |
党员承诺 |
|
 |
党建工作 |
|
 |
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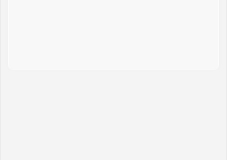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人大专栏 |
|
|
| |
|
□ 范选华
昨晚楼下兜风,同楼道一苏北口音大妈接电话“今年我没得时间回去望稻子,长得个还好啊?”闻言,眼前闪现出氲氤着稻秧香气的故乡来,栽秧那些逐渐模糊的往事又渐次清晰起来。
“细雨燕低飞,栽秧布谷催。”每逢春暖花开、柳林翠绿、草长莺飞的清明到来时,江中小岛拉开了春耕生产的序幕。农人们开始新一轮育种做秧田、耙水田栽秧。
记忆中,父母总是将前一年从颗粒饱满的稻穗上勒下来的稻种拿出来用粪桶浸泡,细心地漂去“瘪子”,剩下饱满的稻种,再放到箩里面用干净的稻草盖上,每天浇上几遍温热的水等待发芽,是为“浸种”。
等待稻种发芽的那段时间,父母也没有闲着,起早贪黑地在秧田里忙碌着。我一直对扬中话“做秧田”感佩至深,这个“做”一字概之,道出了扬中人侍弄秧田的精细程度。扬中人大多将大田当头一小块栽种秧草的地方深耕出来,上水浸泡,整块成畦,施以粪肥,趟平若镜,是为“做秧田”。秧田做好后,父母将已破壳萌芽的稻种小心翼翼、均而匀之地播洒到秧板上,覆之以草木灰,遇到寒凉之季,还要加盖一层薄膜。落种之后,父母或早上端着饭碗、或晚上从厂里疲累归来,都要蹲在秧田半天,直到秧苗尖子齐刷刷地冲破覆盖的薄土层,如一枚枚翠绿而细小的针头直刺头顶的薄膜。这时,他们就会将秧田两头薄膜揭开,让温暖的春风贯穿其中,好让婴儿般的秧苗吸氧透气,这样三四天后,健壮的秧苗就密密麻麻地展露在厚实的秧板之上,精神抖擞地站立在春阳之中。
“青草池塘处处蛙。”进入立夏,不只是池塘,空旷的乡村之夜也被蛙声填充得鼓鼓胀胀。此时,就到了耙田栽秧的时候。耙田,少时的我一直都意会成“霸田”。无论大集体时人工挥锄深耕碾作,还是分田到户后家家想方设法请旋耕机手多耕几个来回,栽秧前都还要将深耕过的水田再耙个三两次。我见过的犁耙长约一米五,架子上有手柄,下有一长排铁齿,形似一把梳子。那些高高低低的泥堆被犁耙“梳”过几遍后,田里平整的象一片片明镜似的,湛蓝的天空倒影在水里,感觉水都是蓝蓝的。长大后才明白,“不怕田瘦,就怕田漏。”耙地这活计很讲究,只有深耕细耙,才能清墒保水,才能防渗保肥。
栽秧,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面朝黄土背朝天,上有“蠓壳子”(一种比蚊子还小的飞虫)盯脸,下有蚂蝗盯脚膀,更有腰酸背疼时,从裤裆里朝后望去,那种永远看不到头的绝望。有着同样感受的父辈们,倒是把栽秧当成农村人亘古不变的程式,坚持着,也创新着。
栽秧,离不开扯秧、打秧。扯秧,大多是年纪大的和女人们的“专利”。她们带着“爬爬老”(矮木凳)和一捆稻草,天不亮就到了秧田里开始扯秧。有人说,扯秧是拔秧苗,母亲教我的却不是这样,右手握住秧苗根部,向上轻轻提起,然后在水里濯净根上的泥土,待左手里洗好的秧苗积累到一定数量时,便用稻草扎起来。扎秧要把握分寸,扎得太紧会伤着秧苗,扎得太松打秧时就会散落。一个个“秧把子”整齐排列在秧田里,小孩子们负责把秧装到笿子里,等男人们挑去打秧。打秧时的男人是最帅的,一手扶着肩头上的扁担,一手拎起秧尖子朝着水田里甩出去,“秧把子”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秧根朝下精准地落在栽秧人需要的位置,伴随着水花四溅的是那此起彼伏的啪啪声。
“手把青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颗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栽秧是苦累活,但也是技术活。因为栽秧技术不过关,母亲没少埋怨我。记得母亲说过,“深耕浅栽出黄金”。如果秧栽得过深就会 “不发棵”,影响稻子分蘖,但栽得过浅,秧苗又会漾在水面上成了 “滂秧”,活不了。母亲还说,“栽秧要栽要戳天罡,千万不栽脚汪塘”,秧栽得过分向前倾斜,风一吹,秧叶子就耷在水面上,这种“斜秧”是很难“活棵”的。不栽脚汪塘,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事,栽秧向后退时脚不能出水,必须在水田里拖着走,拖出两条直笔笔的槽子,而槽子的中间正好栽两棵秧,左右两边也正好各栽两棵秧。
栽秧,我永远记得大集体时的 “拉绳定点”“大兵团作战”,三、四十个妇女在水田里呈梯形状排开来,像是在空中列队飞行的雁阵,妇女们打诨插科的谈笑、指桑骂槐地骂街,那壮观热闹的景象历历在目。栽秧,我永远记得分田到户第一年时的悲凉,母亲打“老虎机”不慎打断右手,在水田边流泪对我的谆谆教诲,“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你只有读书考大学”。栽秧,我永远记得孱弱单薄只有十六岁的姐姐一人栽了两亩田,手丫烂了腰瘫了的苦状。
时过境迁。如今,机耕犁耙、打田栽秧的热闹场景即使在乡下也难得一见。于是,这份浓浓的乡愁就像一根若有若无的线绳,牵着游子那漂泊不定的心,永远朝着回家的方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