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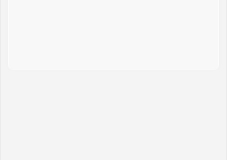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文苑 |
|
|
| |
|
□ 陆尊
早起,看到有人对清明时节雨纷纷最好的解读:因为没有太阳,逝去的亲人才能偷偷回来看我们一眼。世间只有水可以沟通阴阳两界,逝去的亲人都藏在云里。雨落时就会回到人间看看我们,落下的雨滴会把思念带进土里。你以为是雨,其实是亲人思念的眼泪。
父亲陆庭亮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姑妈接到上海打来的急电,告知父亲病危,徐界开车急速地把我们送到镇江火车站,那时还没有高铁,等铁皮火车不紧不慢地到上海站时,已是半夜时分。打的到了普陀区的白玉新村,她们告诉我们父亲已去世一个小时了,没有看到扬中人家常见的呼天唤地的悲凉场景,也没有看到父亲的遗体。遗体被存放到龙华殡仪馆,按规定三天后才能见到。
接下来的三天是最难熬的日子,拥挤的商品房内设起了最简易的灵堂,父亲六十岁生日时拍的正装照放在小桌上,2支蜡烛和几个果盆,小区不让烧纸,只能在脸盆里稍点几个锡箔。父亲少小离家,兄弟四人上海滩打拼,父亲干的是最基层的产业工人,紧巴巴地过了一辈子。阴阳两界,他孤独地睡在那儿,得不到亲人的当面祭奠,此情此景,不禁潸然泪下。
十岁之前,父亲的模样如梦幻一般,只隐隐记得他微胖的样子。父母长期两地分居,终致感情破裂,分钗破镜时我还没记事,却始终知道上海有我的亲生父亲。少年时代,从东新港乘上海班去十六铺,父亲总是带我去外滩、城隍庙白相,回扬时总是将我包中塞满天厨味精和宾馆一次性牙刷和肥皂,上海的亲戚都知道个中原因。期间接到过两次病危通知书,火速赶到六院时,再次见到了他浮肿的脸,肝腹水加肝硬化已将他魁梧的身体折磨得不成样子,好在他总是挺过来了。
父亲六十岁生日,扬中的亲戚去了好多人,其实都预感到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大寿,白玉新村的小屋中被挤得满满,饭店中的寿宴也许是父亲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也是父亲生前我见到的最后一面。
姑爹总是说我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性格和爱好也像,现在我也快花甲,感觉到姑爹的总结九成相符。外貌不用赘述,单就收藏而言,他对我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其实父亲几乎没教过我任何手艺,就连见面,除了老屋拆迁,他在扬中待了月余,其他时间加起来也可能就月余,但强大的基因,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纬度。
父亲一辈子在国棉厂上班,拿着微薄的工资,每月还要寄生活费养我到十八岁。退休时还张罗着让我去上海顶替之事,后因故虽未成行,但这是父亲对我人生规划的真心关爱。据爷叔介绍,父亲是个极为手巧的人,家中的家具都是出自他手,甚至于淘到了一整套老上海落魄资本家家中的红木家具。
回望父亲的一生,平淡、善良、勤奋、普通,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和父亲如同翻模。人生何求,这不正是一生应该的追求吗?
我们陆氏一门,据说清代由苏州阊门移居太平洲,可知曾祖名锦发;爷爷名朝福;父名庭亮,而陆氏辈分为如、锦、朝、廷、纪、昌、顺、德、长、发、其、祥,并无庭字辈。咨询过长辈,原来父亲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大大大廷根,二大大廷美,叔叔廷贵,解放初二大大去上海找工作,后陆续介绍二个弟弟离扬来到上海滩进了工厂。1958年大大大也来到上海,他们背井离乡,父亲和叔叔默认工厂将廷字改为庭字,心中能记得扬中陆姓家庭的存在,这既是长辈的智慧,也是长辈的情商。
二哥耗巨资为父亲在上海立的墓碑,路途遥远,不便每年去祭拜,而哥哥嫂子,爷叔堂哥堂姐一家,都会去擦拭祭扫。每到此时,我都会在群里说些感谢的话,华萍姐总是回道:一家人,应该的。
是啊,一家人,我们都流淌着陆氏祖先的血脉,大家虽分隔沪扬两地,在“一家亲”群中共话家族往事,分享生活点滴,增进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加强了家族凝聚力,使陆家子孙能得到祖先的保佑护,更使陆氏源远流长,更加兴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