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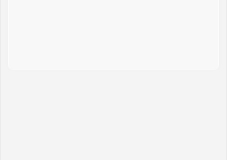 |
|
|
 |
文苑 |
|
|
| |
|
□ 范选华
一场春雨过后,乡野开始泛绿。二月兰盛放的江滩,春和景明,游人如织,这里有忙着刷抖音的网红,有带着孩子踏青玩耍的老人,还有拎着袋子、带个小锹,寻找春天乡野馈赠的“吃货”们。挖野菜,吃时鲜,满足的不仅是扬中人的口腹之欲,俨然成为了一种时尚。
马兰头
小的时候,我是不吃马兰的,总觉得有股“青塌气”。记忆中,马兰不是拿来吃的,而是用于止血。放学后寻(念“qín”)羊草是儿时的“必修课”,贪玩都忘了时辰的我们在着急忙慌之间总会不经意把手指割破了。这时候,就地取材,扯一把马兰头,揉出青褐色汁液后敷在伤口处,就不淌血了。
说起马兰,让我又忆到母亲。当马兰头走上扬中人餐桌成为时蔬后,母亲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把挑马兰、割野藜蒿、摘枸杞头等作为春天里的头等“营生”,成天匍匐在田间地头,蹲寻于江滩水岸。她们吃完早饭骑上三轮自行车,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地出发了。母亲因为右手断臂,不能骑车,只能一路小跑跟上那支队伍。仲春的江滩,芦芽甫出,柳条拂面,那是母亲她们的“战场”。连续多日,从早到晚地蹲趴着,母亲脸都“泡啊”(扬中话,“泡啊”是浮肿的意思),眼睛成了一道缝。偶尔回家一趟,看到母亲脸像“血钵子”,我心生不忍,不禁怨嗔,又不是不给你钱用,何必去吃这个苦。母亲乐呵道:“你不晓得嘎,好耍子呢,一个星期挑马兰、摘枸杞头能卖头两百多钱呢。”我无言,转身抹了把眼泪。因为我知道,母亲挑马兰吃的苦要比别人多得多,她只有左手,而且她只能走着去!
母亲过世后,我还是不太喜欢吃马兰,也许是触物伤怀的缘故。随着如今扬中餐桌上马兰头的频频亮相,我慢慢放下对马兰头的芥蒂之心。
曾经读过周作人的 《故乡的野菜》,提到儿歌:“荠菜马拦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到底是“马拦头”,还是“马兰头”呢?最时髦的办法是到DeepSeek、豆包里寻答案。
其中一种说法是,马兰一般生在田间地头,马儿贪吃其多汁的嫩叶,总是留在原地不肯挪步,所以命名为“马拦头”。明朝的王磐在《野菜谱》中第一次将“马兰头”写成“马拦头”,表达了拦马的意思,马拦头,拦路生,我为拔之容马行。也因为此,后来“马拦头”更是引申出挽留行人之意。清代的袁枚《随园诗话补遗》里记载,汪廷防至上海任官,离任时,村中小童纷纷献上马兰以赠行,一时传为美谈,有人赋诗“欲识黎民攀恋意,村童争献马拦头”。
另一种说法是 《汉语大词典》中“马”有“大”的意思,章炳麟《新方言》:古人于大物则冠“马”字,如马枣、马蜂。而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将马兰描述为 “其叶似兰而大……故名”。清代的顾张思在 《土风录》中也有释义:“马兰,今大叶冬兰也。俗以摘取茎叶谓之头。”意思即为马兰像大的冬兰,且摘取嫩芽部位而食,故俗名为马兰头。
马拦头也好,马兰头也罢,都是饕餮之徒的心头好。无论是挤干剁碎后的香油拌,还是素油清炒,抑或鱼丸高汤汆马兰,都是极致诱惑。这个春天,我有点想吃了。
野藜蒿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诗中的“蒌蒿”,扬中人唤作 “芦蒿”“藜蒿”。在许多扬中人看来,这蒌蒿还有“家”“野”之分。曾经读过扬中朱进龙先生写的 《蒿子圆子》,他说,“家”蒿子扬中人称为“糯米蒿子”,撕开叶子有拉丝的黏液,味清香,是清明节做蒿子圆子的上等材料。“野”蒿子扬中俗称“梨蒿”,有怪味,朱先生说是不可食用的。
“糯米蒿子”我们小时候都挖过,其实很容易与艾草、青蒿等混淆,正所谓“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就像现在的孩子,傻傻分不清韭菜和小麦。野藜蒿我倒是吃过无数次,蒿味浓郁,脆嫩爽口,嚼之有声。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野菜》里说道:蒌蒿,字典上都注“蒌”音楼,蒿之一种,即白蒿。我以为蒌蒿不是蒿之一种,蒌蒿掐断,没有那种蒿子气,倒是有一种水草气。苏东坡诗 “蒌蒿满地芦芽短”,以蒌蒿与芦芽并举,证明是水边的植物,就是我的家乡所说“蒌蒿薹子”。“蒌”字我的家乡不读楼,读吕。汪老高邮人,高邮与扬中一衣带水,隔江而望,不仅语音相近,食味也极为相似。由此看来,汪老口中的 “蒌蒿薹子”也许就是朱进龙先生所说的“糯米蒿子”,而蒿味浓郁的藜蒿才是真正的野菜。
央视二套《健康之路》栏目组曾做过一档《时节之食》的节目,说到清明时节的乡野美食,自然少不了蒌蒿(藜蒿)。节目组请来的植物学博士和营养学专家与主持人 “坐而论道”,作为大自然的馈赠,野生藜蒿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还有黄酮类等生物活性物质,在江南被誉为“开春第一鲜”。因为营养物质含量较高,在烹饪时必须急火快炒,一来锁鲜,二来防止生物活性物质的流失,云云。
食用藜蒿,古已有之。《诗经》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采蘩?于涧之中”,这里的“蘩”就是藜蒿。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里记载,蒌蒿“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以为茹”。蒌蒿虽为野菜,但上层贵族也十分钟爱,《红楼梦》第六十一回里说道,宝玉的丫头晴雯吃厌了肉和鸡,只想吃“蒌蒿炒面筋”这道江南炒素。
其实,野藜蒿不仅可口,药用价值也很高。在我国第一本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对藜蒿的记载,称它全草均可入药;《本草纲目》说其性甘凉,能清热解毒、平抑肝火。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长江边人吃河豚 “但用蒌蒿、荻笋(芦芽)、菘菜三物”烹煮,据说辛弃疾也曾有过河豚搭配藜蒿食用的建议,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里也有类似记载。
枸杞头
《红楼梦》里厨娘与司棋吵架,不仅道出晴雯爱吃“蒌蒿炒面筋”,还说及三姑娘(探春)和宝姑娘(薛宝钗)喜食“油盐炒枸杞芽儿”。
枸杞芽儿,扬中俗称枸杞头,过去很少吃,或许是小岛春鲜太多的缘故,或许是对“外来物种”天然的排斥。这个流淌着西北荒漠基因的 “翡翠野草”,却能在江南水乡安下家落了户,成为春日里的时鲜货,这本身就很神奇。不仅如此,颇为玄幻的是那枸杞头叶,竟能变色,清晨泛紫、正午转碧、黄昏镀金。尤为让人不解的是,这分泌着枸杞碱的嫩叶,食草动物避之不及,人类味蕾却为之癫狂。
国人食枸杞,四季皆相宜。正如 《本草纲目》云:“枸杞春采叶,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明徐光启《农政全书》里也说,“枸杞头,生高丘,实为药饵出甘州,二载淮南实不收,采春采夏还采秋,饥人饱食为珍齑。救饥,村人呼为甜菜头。”其实,对枸杞情有独钟的文人当数苏轼,《小圃五咏·枸杞》就是明证,他对枸杞的偏爱在《后杞菊赋》中更是袒露无遗,“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食之以时,神仙亦羡。春夏之交,枸杞芽、枸杞叶皆鲜嫩多汁,可采之古法炝拌,“嫩笋、小覃、枸杞头,入盐汤焯熟,同香熟油、胡椒、盐各少许,酱油、滴醋拌食”(宋代食集 《山家清供》)。也可“简单粗暴”地来个清炒枸杞头、枸杞头炒鸡蛋,还可以老母鸡汤汆枸杞头、枸杞头汤汆肉圆子,所谓“市井烟火人间味,怎么好吃怎么来”!
春日的扬中,舌尖与自然在这里约会。蓝绿交织的江中小岛,用一篮篮时令鲜味,将春日的生机与烟火气浓缩成餐桌上的诗情画意。是啊,扬中的春天,在枝头繁花,也在乡野时鲜。趁着春光正好,何不提篮寻鲜,赴一场舌尖与春水、乡野、清风共舞的盛宴?
|
|





